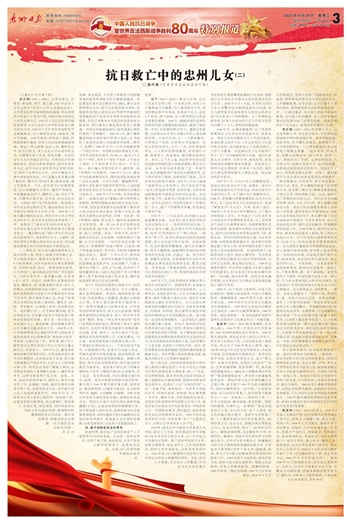□ 袁代奎 (作者系忠县政协退休干部)
(上接8月13日第三版)
任正炳(1911~1984),又名任蔚文、任畏吾、郝远猷、郝孑、黄玉清,1911年出生于忠县王场乡(后划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在忠县东区中学读书时经吴逸僧、牟汤铭培养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秋任西界沱小学党支部书记,1930年3月任忠县第四届县委委员,9月忠县县立中学校长陈孟仁聘为该校文书,1931年1月中旬因李叔昭在万县被捕叛变,任正炳和吴永浩、成政安、黎永升被捕。1932年秋初,经陈孟仁营救,托病请假狱外就医,其家人向县府诳报溺毙销案。陈孟仁资之旅费,远赴上海,辗转到北平,改名任蔚文,考入北京大学法商学院念书,与谭蜀贫接上关系,恢复党籍。先后担任中共北平西城区委书记、共青团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团河北省委巡视员、团河北省军委书记,在中共河北省军委书记老周(阎红彦)领导下从事军运工作。1933年被派任天津市委组织部部长,与巴县籍女党员董启翔(董启容、董平沙)扮成夫妻,组成家庭,建立市委机关。不久,因市委书记吴佩苍叛变,任正炳被捕关入黑牢,遭到严刑拷打。年底越狱逃出虎口,辗转到上海,结识了张庚、吕骥等左翼作家、艺术家,涉足文艺活动。王国权(康午生)给他寄来一张河南大学毕业生郝远猷的文凭,建议他用此名去日本留学以做留日学生的工作。1935年3月他与董启翔到达东京,考进日本大学文学院社会科学习,在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下工作。他参加了“留东京社会科学研究会”,实质是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并成为主要领导者之一,董启翔也成了留日学生妇女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他们同任白戈、王阑西、雷任民等同志积极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卓有成效说服留日同学归国参加抗日救国运动。
七七事变后,任正炳与董启翔带着女儿洛沙回到上海,参加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任正炳改名郝孑,被选为主要领导人之一。9月转到南京,与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取得联系,受到叶剑英、陆定一等领导同志接见。10月参加“上海内地流动宣传队”并任副队长,与团长李竹平一道率董启翔、石雪书(女)、石竹、华兆江、侯枫等人冒着敌机的轰炸,辗转苏、浙、皖数省城市农村,深入人民群众,宣传组织群众抗日救亡。1938年初国民党政府要归国留日同学集体到中央战干团受训,郝孑便离开救亡会,参加了张庚同志率领的蚁社救亡演剧队,辗转苏、浙、皖一带的城乡,从事救亡宣传,发动群众抗日。他们溯江而上,在芜湖时董启翔、范吉仙等赴延安,后来董与延安中央党校组干班毕业的钟国松结婚。郝孑及一部分同志往安庆渡江北上,重返舒城,担任舒城县第四区区长兼区抗敌动员会主任。1938年4月,中共豫南特委书记兼新四军第八团政委王盛荣派他到光山绿林武装“豫南游击纵队”作参谋,从事兵运工作。同年夏,郝孑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到中共长江局书记董必武同志,听取指示。1939年6月,董老来舒城视察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民众教育馆向青年作时事报告,又单独同郝孑谈话,指示他不要暴露共产党员身份,以民主人士的面貌从事工作,利用合法身份了解敌人情况,运用我党灵活的斗争策略打击敌人,掩护革命青年,这样也更有利于抗日统一战线。后来,他担任县政府秘书、副县长,领导当地宣传工作,出版救亡报纸,秘密发展电台报务员等入党,直接负责县大队,对开辟大别山区工作起到重要作用。1939年11月,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率王阑西等一批军政干部,由延安到皖东根据地,经过舒城时,接见郝孑,听取汇报、肯定成绩,同时指出存在的缺点和注意的问题,强调要时时警惕国民党反共逆流。郝孑深受教育,积极采取应变措施。12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省动委会、工作团干部数百人经舒城等地向皖东皖南皖北抗日根据地撤退。亲近我党的进步县长陶若存已调走,继任县长陈常倾向反共,郝孑以县政府秘书身份,获取国民党《防止异党办法》等密件和被国民党掌握的共产党员名单及特务的秘密活动情报,交给已发展为中共党员的县政府电台报务员,及时通知已被监视的党员干部撤离。当同志们脱离险境后,他才绕道山路经叶集到了河南横川。1940年6月,郝孑辗转撤退到皖北涡阳新四军第六支队,10月组织上派他到由第六支队随营学校第二期学习,该期于1940年11月7日在永城麻冢集一个村庄开学。学员既有部队和地方干部,又有外来的知识青年,约900人,编为2个大队7个中队,其中3个部队干部队、1个地方干部队、3个知识青年队(其中一个女生队)。郝孑编入军事大队学习,兼任第一队(军事队)文化教员。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统一整编新四军,改第六支队番号为新四军第四师,六支队随营学校改名抗大四分校,彭雪枫师长仍兼四分校校长。1941年5月2日晚,四分校奉命随十一旅通过宿(县)蒙城公路日伪军据点封锁线,转移到蒙城北面的苗庄待命东进。3日晨,国民党顽固派李品仙部两个骑兵团正渡过涡河向苗庄逼近,形势十分危急,教育长刘清明从全局考虑,令第一大队第一队(军事队)牵制、阻击敌人,掩护校直属队和女生队突围。第一队110多名学员都是部队选送的营、连干部,其中有十几名红军干部,战斗力很强。但这一带是平原,有利于敌骑兵的运动,且全连唯一的轻机枪出了故障,火力大为削弱。一队同志坚定沉着,发扬抗大“英勇牺牲”的战斗精神,以屋顶、树干和墙基为依托,用步枪、手枪和手榴弹顽强抗击敌人。激战一个多小时后,弹药耗尽,伤亡很大。连指导员杨致平甩掉手枪,捡起牺牲战友的步枪,从屋顶跳下,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全队士气大振,学员们个个犹如猛虎扑食,与敌人经过两个多小时殊死搏斗,终于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掩护校部直属队和女生队安全转移。
在3个月的反扫荡和反顽战斗中,四分校伤亡二三百人,损失很大,不少人被俘,郝孑也因伤被俘。审讯时,他自称姓名“黄玉清,抗战初期由上海撤退,取道江北回湖北江陵,不得已留在新四军中搞财务工作”,始终未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中共党员身份和革命经历,敌人也无法查清,便将他及被俘同志押赴西安,投入“西北青年劳动营”甄别、审查。“西北青年劳动营”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地方,那里除了惨无人道的刑具外,还有许多莫名的凌辱与身体折磨。在饥饿、劳累、重刑下,许多人丧失了生命,掩埋在劳动营西荒野土丘,人称乱葬坟。任正炳一直坚持原来的口供和黄玉清之名,一个爱国抗日的热血志士,一个坚贞的共产党员,不能驰骋沙场,高举大刀向敌人砍去,而被关进黑牢中饱受摧残,他何等愤怒,挥笔为文,控诉国民党卖国投降派。按集中营规定,两年后如无特殊身份,即可放出回家或在当地谋生。他在集中营认识了同被关禁的地下党员、《建国日报》社长吴焕然,结下友谊。吴先期出狱,仍任《建国日报》社长,找到一名任中校教官的留日同学担保,黄玉清于1944年夏才离开集中营,重获自由,被吴焕然招入《建国日报》社,先后担任资料员、编辑、主任编辑、总编辑。1946年他在西安街头碰见原蚁社救亡演剧队队员范吉仙。范的丈夫是中共西北局社会部的赵耀斌(石坚),由延安派到西安搞情报工作。范介绍他接上组织关系,赵吸收他为社会部秘密调查员,利用《建国日报》总编辑的社会地位和有利条件,收集敌人动态等机密情报,由赵直接领导,从此战斗在隐蔽战线上。
四、踏平艰险赴延安的青年
抗战时期,延安成了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爱国青年向往的圣地。忠县的一些热血青年,历经千难万险,奔赴延安,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下,直接参加抗战。这里,讲几位青年踏平艰险赴延安的故事。
马丁(1913~2012),原名马洪英,出生于忠县石宝坪山坝一个书香之家,其伯父马子尊和叔父马德尊、马仁庵均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他是家中长子,还有3个弟弟、两个妹妹,从小便受到民主和进步思想的熏陶。1930年,他随在国民党部队任职的四叔马德尊到驻地南昌,就读于南昌第一中学,在校期间努力学习。遵照父亲意愿,马洪英1931年考入学制6年的上海东南医学院。入校不久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了沈阳、长春等20多座城市。全国人民怒火冲天,北平、广州、武汉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群情激愤,纷纷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发表通电,强烈要求政府抗日。28日,几千名上海、南京的学生前往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对日宣战。18岁的马洪英参加了这一革命行动,初次接触到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宣传,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思想得到了提高。因马洪英突出的进步表现,1933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学运工作负责人、四川老乡刘开基(化名)将他纳为考察、培养对象,马洪英更加积极地参与党的活动和学生运动。为方便开展工作,他将自己的租房作为会议地点。在学生运动中,马洪英还结识了李维汉的二女儿、地下工作联络员李曦,更加靠近中国共产党。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抗日救亡运动迅速覆盖全国。马洪英已是东南医学院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他率同学们走出校门,到市区游行示威,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高呼“打到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还率队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深入乡村进行抗日宣传。在南京游行、抗议时遭到军警镇压,游行队伍被冲散,很多人被抓捕,他躲到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的姑父家,才逃过一劫。但与刘开基、李曦失去联系,后来他按刘告诉的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地址找到李克农,要求去延安。李克农说:“你是学医的,回到学校也可以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等拿到党组织介绍信再来找我们。”
1937年7月,马洪英和同学史敏言考入南京中央医院实习。因成绩优秀,业务能力突出,马洪英很受院长沈克非的赏识。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敌机不断进入南京市区,南京中央医院收治大量抗日受伤将士。10月沈院长奉命将医院西撤经武汉至长沙,马洪英和史敏言、任国祥、朱仲丽、陈应谦等东南医学院的同学随南京中央医院撤离上海。途中他们一边为伤员清创换药,一边宣传抗日,鼓励伤员愈后重上前线。在长沙,他和同学们在伤员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得到八路军长沙办事处的支持与帮助。在了解他想去延安的愿望和在校期间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的经历后,长沙党组织决定发展其入党,马洪英履行了入党手续,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国民党特务也准备抓捕他,党组织通知他紧急撤离长沙。当时军警已将医院重重包围,他躲在沈院长车子后备箱中逃离虎口。
到了武汉后,马洪英拿着党组织介绍信到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和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接上了关系。在汉停留期间,很多学生想去延安寻找抗日救亡道路和抗日救国真理,党组织安排他带领这批学生,由武汉“八办”介绍到西安“八办”,完备手续,奔赴延安。马洪英不负组织信任,带领任国祥、朱仲丽、陈应谦等数十名学生,辗转万里,历经艰险到达延安。党组织分配他到陕西旬邑陕北公学工作,成仿吾校长安排他当学生队指导员、学校医务主任。但因路远事多、情况紧迫,他的党组织关系在层层转接中丢失。1938年初由成仿吾校长介绍,马洪英取“兵丁”之意改名马丁,在陕北公学再次加入共产党。
1939年,陕北公学与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4校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马丁任学校卫生处副处长等职。除了承担学校医疗任务、给群众看病外,他还为护士、卫生员授课培训,将护士培养成医生,卫生员培养成护士。1941年底,马丁被调到马克思列宁学院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做理论研究。当时,医学人才紧缺,后方医疗工作繁重,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把他调到卫生系统,安排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与北岳区党委合办的卫生队。1942年5月1日起,日伪军出动5万余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25日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牺牲。马丁带领的包括伤员、医务人员在内的几百人队伍在突围后只剩下十几人,最终回到根据地。
1944年冬,由傅连暲推荐,马丁再调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先后任医政科长、医政处长。军区卫生部对整体卫生工作进行指导,各地的群众医疗卫生工作也由军区卫生医疗机关承担,战场救护加上人民群众医疗,工作十分繁重。在组建边区卫生学校等工作中,马丁与马海德经常打交道。他以白求恩大夫为榜样,尽职尽责、救死扶伤,深受伤病员的爱戴和领导的器重。在延安马丁和四川老乡傅崇碧、田家英十分交好,他的夫人杨远和傅崇碧夫人黎虹也是一同去延安的同乡同学。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决定以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马丁随中央工委辗转华北。1948年,晋察冀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马丁担任军区卫生部医政处长,参加了解放北平(今北京)、天津、张家口地区。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马丁随中央领导进入北平。中央成立了以叶剑英为主任的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马丁是军管会下设的卫生接管部成员,负责接管国民党陆军总医院,他身兼华北军区卫生部医政处长、陆军总医院院长和军管会成员三职,重担在肩。因为行政管理经验丰富,专业知识深博,对接管政策掌握恰当,他为维护医院稳定做了很多工作,日本和国民党留下来的医务人员对他都很信服。在他的管理下,医院很快投入使用,收治大量伤员。先后更名的华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北平陆军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都由他担任院长。1949年由他组织撰写、华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主编的《军医提挈》,即后来的《军队临床操作常规》一书出版,成为全军第一部医疗技术操作常规,对全军医疗卫生事业正规化建设起到了划时代作用。
1955年,马丁荣授上校军衔,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中国人民解放胜利二级解放勋章,1960年晋升大校,成为开国大校。1959年秋升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1979年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部长,1983年以副军职离休,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勋章,一生为抗战救护和新中国军队系统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莫延年(1920~2004)原名莫肇昭,忠县拔山镇人,1934年考入忠县县立中学第29班,1937年转到成都协进中学读书。1938年改名莫延年,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到富县进入通讯学校,毕业后于1939年参加八路军,编入129师385旅172分队电台作报务员,开赴抗日前线,在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他多次向家中写信,述其忠党爱国之志,表示“努力呀!在烽火中锻炼,求得自己的进步”“母亲:怎样慰藉你啊,报答你啊!哎,我只能将你那慈祥的心,融化在人类解放事业的光明”“要诸妹继续读书”,并动员大妹肇瑜等投奔延安。莫延年原与永丰乡梁寿疆之女文棠订婚,梁文棠于1930年冬提出解除婚约,他回信嘱梁自决。信中说:“目前国家危险,吾人的责任更重了,我目前是不能离开它——这一支铁流——革命的斗争……许多父老姐妹,颠沛流离,骨肉四散。而我们的离别,又算什么一回事呢?”表达出他舍自己小家、为人民大家,舍个人爱情、谋人民幸福之博大情怀。莫延年历任军委三局、十八集团军前总太行军区报务员,129师报务主任,电台台长,跟随刘邓大军转战太行山,抗击日伪军,经历了129师的历次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解放军17师、57师师长。解放后,莫延年先后任空军司令部通讯处长、空军司令部训练处长、新疆建设兵团石河子指挥部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军电讯工程学院(空军工程大学)副政委、政委,参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条例》的修改工作。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成为开国大校,荣获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中国人民解放胜利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勋章,1983年以正军职离休,2004年4月17日因病逝世,党和人民给了他高度评价,说他是“我军革命战争年代少有的知识分子,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与得失,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生清正廉洁,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人民空军通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军队通信工作者。”
李正清(1917~1971)忠县磨子乡人,从忠县明新小学、忠县县立初中、万县师范读到成都华西协和高级中学。面对军阀混战、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现实,他愤愤不平,又不知出路何在。七七事变爆发后,李正清和爱人陶顺文商量,一起去延安,约10月底,他俩从成都出发,到了西安,找到“八办”,很快办完了手续。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山川,他俩无钱坐汽车,全凭两条腿,还要通过国民党的层层关卡。但他们下了决心,再困难也要去延安。在路上,他们碰到不少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一路风餐露宿,历经艰辛,终于到达延安。经过口试、笔试,李正清被录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成为第三期学员;陶顺文被录取进入陕北公学,两校相距不远。从此,他们开始了军事化的学校生活。当时抗大学员编为军事、政治、女生3个大队,李正清被分到政治大队。政治大队的课程安排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教员有党中央领导同志,也有从大后方来的知识分子,李正清听取了毛泽东讲政治形势报告、艾思奇讲哲学、任白戈讲政治经济学、滕代远讲战略学、罗瑞卿讲军队政治工作。1938年夏天,同学们从抗大毕业,都争先恐后报名上前线,投入到抗日的战火中去。不巧的是李正清胃病再次发作,吐血不止,但他还是坚持要求到前线去。抗大副校长兼教育长罗瑞卿找他谈话,关心地询问他的病情,亲切耐心地劝导他说:“你的病这样重,目前延安医疗条件太差,前线更差,补血的针药无法找到,你还是回四川去,一方面治病,一方面直接和当地党组织联系,做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不管在哪里,都一样干革命嘛。”亲笔为他写了介绍信,叫他到重庆找吴玉章。临行前,可巧毛主席来到抗大给学员作报告,报告结束时,学员们纷纷请毛主席为自己的纪念册题词。毛主席很高兴,当即挥笔一一题词。为李正清题写了:“团结干部,联系民众,是一刻也不应该忘记的。如果这样做,就有了工作胜利的基础。”其他校领导也在他笔记本上题词赠言。罗瑞卿的题词是“把握现有优良条件,克服困难,以完成解放民族之使命。”许光达的题词是“掌握斗争的艺术,以少的力量战胜多的敌人,以小的牺牲获得大的胜利。”滕代远的题词是“我们是抗大的优秀学生,我们是抗战的先锋战士,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而斗争。”徐以新的题词是“创造新中国是我们的目标,为着这一目标,任何艰难困苦和牺牲在所不惜,而且抱定必成必胜之信。”
李正清回到重庆,吴玉章热情接待了他。他牢记领导同志的教导,一面治病,一面自学《资本论》等马列经典著作,找到当教师的社会职业,先后在辅仁中学、青木关中学等校任教和当教务主任,秘密联系附近大中小学的进步教师和学生,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先后担任农工党重庆市委委员、副主任委员。1950年李正清被求精商学院、正阳法学院聘为教授,讲授政治学和社会发展史,不久又担任正阳法学院院长兼教务长。1952年调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授,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等课程。
陈其祥(1913~2011)忠县人,193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成都市共青团南区工委书记;同年11月被捕入狱,坚贞不屈,判刑5年;1938年1月出狱后,得知中共中央在陕北、在延安,心中坚定地升起一个念头:我是共产党的人,到延安去,找到党中央,参加革命队伍,参加抗日,为伟大理想奋斗!他历尽艰险,跋山涉水,辗转千里,奔赴延安,先后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陕北抗大三分校学习;1942年3月毕业到八路军印刷厂工作,任后勤政治处干事、党总支部书记;1946年11月任职延安药厂。参加1949年12月西南服务团,担任党总支部书记、大队长;历任四川省重庆市总工会、市搬运公司副经理、市建委集修处党支部书记、副处长;1983年1月离职休养,于2011年8月24日逝世,享年9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