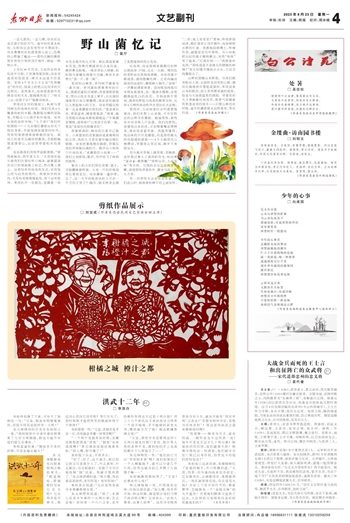□ 聂厅
一会儿落雨,一会儿晴,母亲说这是长菌子的好天气。童年时的夏末秋初,太阳雨总会在劳作中不期而至。雨水裹着松针的清香渗入泥土,仿佛给山野施了魔法——那些沉睡的蘑菇便在夜色中悄然顶开腐叶,撑起一柄柄小伞。
上世纪80年代末,父亲所在的单位连年亏损,工资薄得像层纸;母亲卖泡菜的钱筐里,硬币永远盖不住筐底。家里4个半大小子正是“吃垮粮仓”的年纪,饭桌上的愁云比雨季的天还阴沉。直到某天,母亲望着窗外忽晴忽雨的天光,眼睛倏然亮了。“明天上山,捡菌子去!”她激动地说。
茅塔河左岸的缓坡上,枞树与青冈树交织成绿色穹顶。我们兄弟4人攥着防蛇的木棍,像勘探宝藏的冒险家,用棍尖小心拨开松针地毯。突然大哥的惊呼炸响:“九月香!”我们呼啦围拢——十几朵橙红蘑菇从松毛下探出身来,伞盖饱满如盛放的牡丹,背面的皱褶透着蜜蜡般的莹光。最动人的是伞尖凝结的露珠,手指轻触便滚落掌心,沁凉里带着松木的清甜。
母亲教我们用指甲掐断菌根:“留得根脉在,明年重又生。”大哥顽皮地示意我们往菌坑啐口唾沫,就像猛兽在自己的领地做上标记,然后覆上薄土。这看似有些诙谐的仪式,实则是山民与自然的契约。我很快学到诀窍:凡见松毛微微隆起处,底下必有乾坤。果然扒开一处鼓包,竟藏着一朵未完全展开的九月香。鲜红菌盖紧裹如花苞,仿佛丹霞揉碎后点染而成。捧到鼻尖轻嗅,一缕奇香钻入肺腑,似松脂与蜜糖在晨雾中交融,难怪乡谚赞它“放一片,香一锅”。
更深的山林里,青冈树下藏着另一番天地。青冈菌如罩着青纱的仕女,菌褶层叠似百褶裙;虎掌菌肥厚敦实,黑白云纹在伞盖上晕开;石灰菌则通体雪白如石膏雕塑,圆滚滚的菌球让人想起缩小的月光。母亲用棍尖指着一丛金黄蘑菇对我们说:“莫采黄包皮,看着富贵,嚼着像柴渣。”接着,她又用棍尖挑起朵紫斑菌抛远:“牛屎菌穿绸缎,毒得很!”山里孩子的第一课,便是“美丽往往暗藏杀机”。
背篓渐满时,林间的白雾早已散尽。小弟篮底的虎掌菌挤成黄褐相间的云团,我的九月香在篓中铺出橙红锦缎。母亲把篓绳勒在胸前,背篓压弯的脊梁像拉满的弓。歌声从小弟弟口中淌出来:“采蘑菇的小姑娘……”我们立刻接唱,歌声、笑声惊飞了树梢的斑鸠。
集市上的主妇们围住背篓、篮子,手指翻拣着野菌。五毛一斤的价格很快让篓底见空。母亲攥着一叠钞票,乐了,这一大早的收获快赶上父亲一个月的工资了!随后,她又转身去割了条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灶房里,母亲将顾客挑剩后的野山菌洗净、归拢,足足一大碗。琥珀色的菜籽油在铁锅里沸腾。母亲将菌子撕成条,菌肉脆嫩色鲜。五花肉煸出晶亮的油泡时,蘑菇倾入锅中,“滋啦”一声爆起满屋异香。菌肉吸饱肉脂后变得金黄透亮,加一瓢清水慢煨,汤里翻腾起乳白的浪花。当锅盖掀开那刻,菌香的野性与肉香的醇厚交织,兄弟4人喉结滚动的声音竟比灶火还响。
前两年,父亲病重时念叨着要喝菌汤,我们本想上山采摘,可市区附近的山野没有蘑菇。跑遍菜场,最终在市郊寻得几斤杂菌。我们没想到,杂菌炖出来的汤,父亲咂着嘴连赞鲜美,皱纹里漾着笑意。我猛然懂得:他品味的不只是蘑菇,而是那些被太阳雨浸透的清晨——4个小脑袋在山林攒动,背篓里山货沉甸,脚步下希望丛生。
而今超市货架上鹿茸菇、杏鲍菇、金针菇泛着人工栽培的冷光,标注着“富含β-葡聚糖”“绿野山珍,人间至味”等字样。可我的舌尖总在雨季苏醒,渴望那枚带着松针、露水与泥土的九月香。
有一回带侄女去县里走亲戚,我们进山时,她指着松林下的土地惊呼:“二伯,地上有星星!”原来,昨夜新雨润泽,橙红菌伞正顶开腐叶,宛如朝阳点燃的灯盏。我教她掐根覆土,啐唾作祭,就像哥哥当年那样。当小姑娘把沾泥的菌子捧到鼻尖,突然“咯咯”笑了起来:“它真好闻……”我接着补充到:“那味道是不是像太阳晒暖的树林!”侄女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兀自寻找蘑菇去了。
山野的馈赠从未断绝。当我们俯身贴近土地,总能听见自然的心跳:菌丝在腐殖质中蔓延成银河,季风送来云朵的眼泪,而人类弯腰采摘的弧度,恰是与大地最温柔的拥抱。背篓里的九月香静静吐纳芬芳,那香气里藏着所有迷途者的故乡——只要山林仍在呼吸,童年的蘑菇便永远转着弯,等在归途。 (作者系忠县永丰镇人)